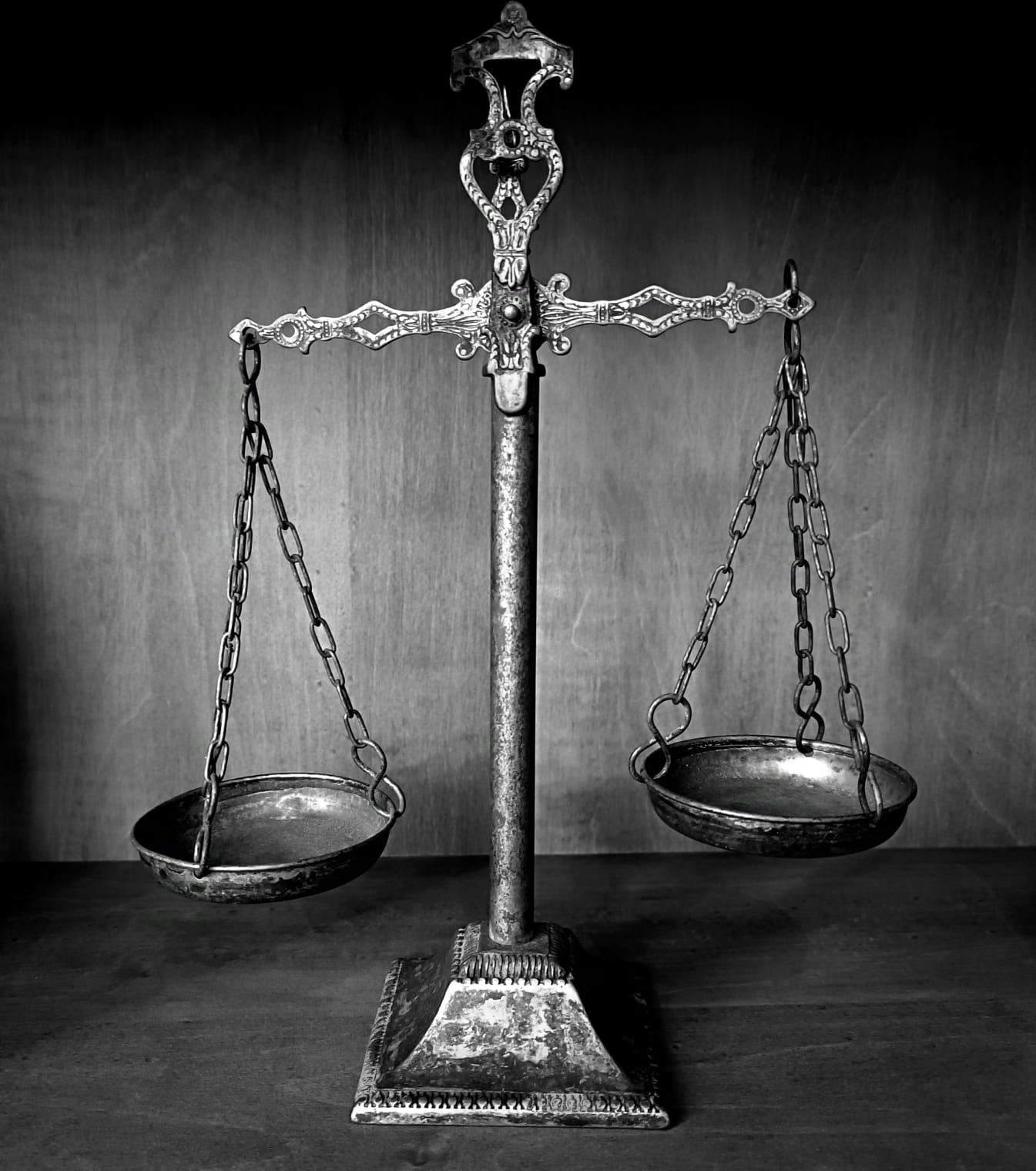新闻
案例更新: - 终审法院就《防止贿赂条例》第30(1)(b)条的涵义作出裁决
2025年4月11日

在2025 年 4 月 1 日,终审法院以大比数3 : 2 裁定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林」)三项披露受廉政公署调查之人士身份的罪名,违反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贿赂条例》第 30(1)(b) 条。
背景
林曾亲历2019年7月21日在元朗地铁站发生的白衣人士袭击黑衣示威者的事件(俗称「721事件」),并受廉政公署邀请以证人身分协助调查。廉政公署在会见林时表示,他们正对一名名为游乃强的警司(「游」)进行调查,他涉嫌贿赂罪(《防止贿赂条例》第II部所订罪行)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非《防止贿赂条例》第二部所订罪行)。林亦被提醒《防止贿赂条例》下禁止披露的规定。
林其后分别举行了三次记者会,每次均披露游因「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非第II部分罪行)而接受廉政公署调查。由于这些披露,林被控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 30(1)(b) 条,泄露了正在调查的对象的身份。林最初被裁判官定罪,但其后上诉至原讼法庭,上诉得直获撤销判决。律政司其后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提出以下问题:
「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 201 章)第 30(l)(b) 条,尤其是『该项调查的标的之人』一语的正确解释。当被告在明知或怀疑受调查人正因第II部所订罪行而受调查时,披露了该受调查人的身份及该受调查人正因一项非第II部所订罪行而受调查时,被告人是否已违反《防止贿赂条例》第 30(1)(b) 条。」
因此,终审法院的任务是诠释《防止贿赂条例》第 30(1) 条的含义,该条规定
(1) 任何明知或怀疑正有调查就任何被指称或怀疑已犯的第II部所订罪行而进行的人如无合法权限或合理辩解,而向 ——
(a)该项调查的标的之人(受调查人) 披露他是该项调查的标的此一事实或该项调查的任何细节;或
(b)公众、部分公众或任何特定人士披露该受调查人的身分或该受调查人正受调查的事实或该项调查的任何细节, 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4级罚款及监禁1年。
大比数判决
李义常任法官颂布了多数判案书,而张举能首席法官和欧颂律非常任法官分别做出了一致判决。
李义常任法官在其判决中首先将第 30(1) 条分为两部分,即犯罪意图部分 (mens rea) 和犯罪行为 (acus reus) 部分。犯罪意图部分规定被告人知悉或怀疑有人正在对「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 II 部被指控或怀疑犯有的罪行」进行调查,而行为意图部分规定被告人确实向被调查的人、公众、部分公众或任何特定人士披露「被调查人确实受到调查」或「该调查的任何细节」。在这宗上诉中,终审法院关注的是犯罪行为部分,因此问题是,被告只需披露该人正在接受廉政公署的调查就足够了吗?还是被告必须进一步披露该调查是「针对指称或怀疑已根据《防止贿赂条例》第二部所犯的罪行」?如下文所述,终审法院在多数判决中倾向于前者而非后者的诠释。
随后,李义常任法官提出了对第 30(1) 条的两种可能诠释。第一,从字面解释来看,需要揭露对第二部分罪行的调查。第二种诠释是重许条文的文意及目的,仅要求揭露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存在。 李义常任法官更倾向于第二种诠释,因为它更准确地反映条文的立法原意,即维护廉政公署就贪污罪行所作调查的效能和公正性,以及保护受调查人的声誉。与犯罪意图要求不同,犯罪意图要求被告知悉一项就第II部所订罪行之调查正在进行,以此确立被告的思想状态应受谴责,犯罪行为要素是客观的,旨在维护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完整性。此外,第二种解释考虑了无需明确披露所调查罪行的性质即可间接披露的情况(判词第 39-42段 )。
此外,张举能首席法官在其赞同裁决中认为,第二种诠释更为宽泛,且在相关条文下也是允许的,因为《条例》第30(1)(b)条的中文文本为“该受调查人正受调查的事”,因此相关的禁止披露仅与某人是调查对象这一事实有关。
不同意见
霍兆刚常任法官在其不同意判决中指出了第 30(1)(b) 条规定禁止三种不同类型的披露。虽然每个类别旨在解决不同类型的行为,但它们之间存在一些重叠。此外,所有类别均包含「受调查人」一词。值得注意的是,「受调查人」的定义包含了该人是「该」调查的对象这一事实,这又引用了第 30 条的引言「针对根据第二部分被指控或怀疑犯下的罪行的调查」。因此,「受调查人」只能指因「根据第II部分被指控或怀疑犯下的罪行」而接受调查的人。因此,禁止揭露「受调查人」只能意味着揭露正在接受第II部分罪行调查的个人身分。
因此,对于第30条来说没有其他诠释(即上文的第二诠释)。即使存在,从目的性角度来看,第一种诠释仍然比第二种诠释更受青睐。如直接阅读 1996 年之前的版本就会发现,与目前的版本相比,禁止的范围有所缩小。现行第 30(1) 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根据第 II 部分被指控或怀疑犯下的罪行的调查」的完整性,而不是更广泛地保护廉政公署的调查。林文瀚常任法官同意霍兆刚常任法官的观点,同时认为第二种释范围太广,因为它禁止范围太广泛,只要满足先决条件,即:1)正在对相关人员进行第二部分调查;2)披露信息的人知晓或怀疑有此类调查,即使仅披露该人正在接受刑事调查,甚至没有提及进行调查的机构估也会违反相关条例;然而,这种诠释太措辞过泛,超出了第 30 条的措辞范围。
结论
如上文所述,多数判决仅以3-2的微弱优势胜出,因此相关条款的解释绝非简单或直接。然而,就目前情况而言,第二种解释是目前的法律,就第 30(1) 条的目的而言,禁止披露不需要涉及第II部分的罪行。但必须留意的是,因为此案涉及当事人同时因第二部分罪行和非第二部分罪行而接受调查的情况。当有两项完全独立,且不同的调查因不同且毫无关联的事实而起时,一项调查涉及第二部分罪行,另一项调查则不涉及第二部分罪行,且相关披露仅涉及后非第II部分的罪行,则同一法律是否适用于此种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且终审法院尚未作出决定,正如张举能首席法官在判词第 10 段中明确指出。
有关判词可参见这里。
联系我们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帮助。
让我们知道如何共同努力实现您的目标。